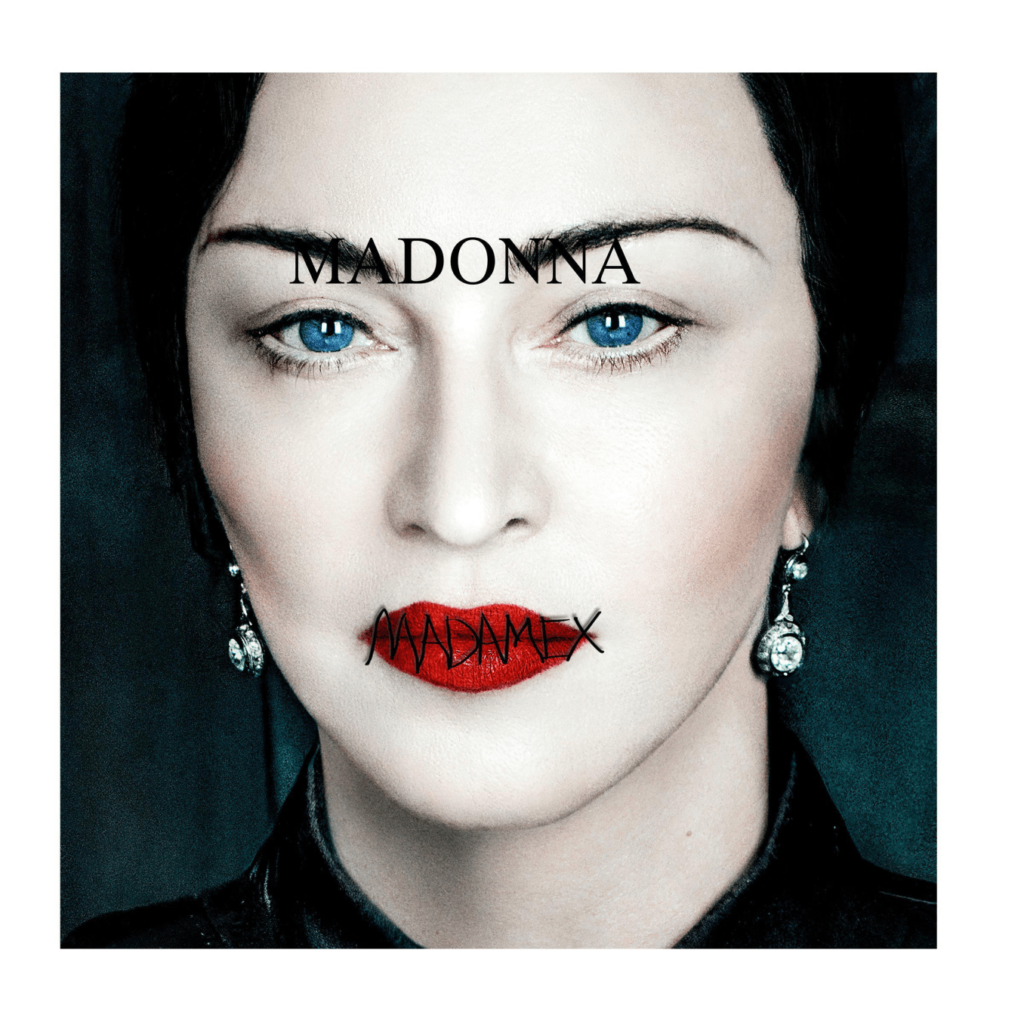IG一秒生存攻略
「老人家才會玩FB(Facebook)!」 多得較早前某家補習學校拍攝的網絡視頻,街訪了好些00後,大家都異口同聲宣布FB已步入侏羅紀時代,於是,為怕錯失下一代消費者的商機,不少當廣告客戶的朋友都問:「我們是時候開個IG(Instagram)或Snapchat帳號嗎?」 事實上,2014年左右,我已陸續替部分客戶經營IG帳號,當時,品牌在摸著石頭過河的狀態下,只可讓帳號自然增長,直至兩年前左右,IG才開始正式商業化,推出不同廣告產品。品牌現在終於開始可以在IG打廣告了,加上不斷推出如IG Stories及FollowHashtag等新功能,旋即令這社交平台成為品牌的寵兒,但問題是,站在品牌營銷的角度,此消彼長下,距離IG取代FB的日子,到底還有多遠? 我認為,投入IG營銷前,品牌經營者有幾點是先要注意的: 一、你目前的目標客戶群,主要活躍的平台在那裡?不要為了追潮流,而分散自己的注意力及浪費資源,按目前香港的情況來看,FB還是眼球集中地。 二、的而且確,按目前用戶習慣的趨勢,Engagement在FB的世界只會持續降低,廣告客戶追數的難度高了,但要留意,即使轉到另一個較受追捧的平台,這依然是一個不能改變的用戶生態。 三、除非是直接和Influencer合作,否則,作為品牌帳號,Engagement在IG的世界,隨時會比FB更低,再者,IG用戶的注意力,一般會比FB更短。 四、影像先決是IG重點,如果三秒法則適用於FB,關鍵時刻在IG就可能只有一秒,你會放怎麼樣的圖片、文字、色彩、動態影片等創意來吸眼球?直接把FB的內容放到IG?相信此路不通。 五、不要期望在IG打廣告,就可以獲得較高的Engagement,那個同樣是追接觸率的廣告遊戲,尤其是用戶注意力極短的IG Story,可是,品牌卻可以藉此建立形象,以及接觸到較年輕的社群。 《原文刊登於2018年2月晴報》